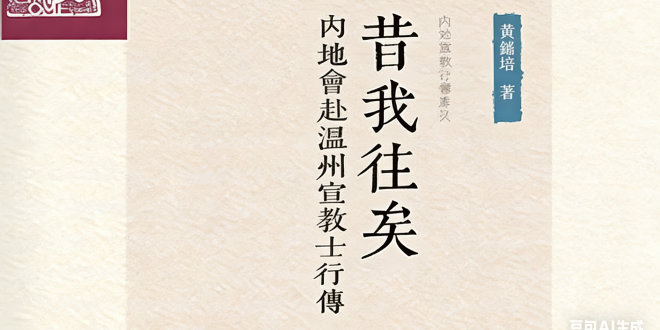文/恩雨
一本小书
《昔我往矣——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》是黄锡培老先生于2014年所著的一本小书。全书只有120页,却蕴含着内地会温州宣教区从1895年到1950年的历史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出自《诗经》,在出征与归来的时空交错中,深刻道出了战士们久戍边疆、思念家乡的心境。黄老先生以此为题,是为感念昔日赴温州的宣教士们披荆斩棘、舍己服事的福音精神。
温州1867年开教,1876年开埠,最早前来传道的是内地会差派的宣教士曹雅直(Mr. Scott),此后又有蔡文才(Mr. Josiah Alexander Jackson)、稻惟德(Dr. Arthur Douthwaite)等人陆续来到。[1]从1867–1950年,算上宣教士病逝于温州的儿女,受内地会差派来温的共计74人。黄老先生从中选择了八位宣教士来书写他们的故事。这八位宣教士分别是:衡平均(Mr. Edward Hunt,1897–1921年在温州服事),衡师母魏思忠(Mrs. Alice Hunt,1890–1921年在温州服事),梅启文师母(Mrs. E. I. Menzies,1892–1914年在温州服事),谢姑娘(Miss Kathleen Stayner,1893–1906年在温州服事),夏时若(Mr. George Hugh Seville,1903–1919年在温州服事),夏师母江孟氏(Mrs. Jessie Merritt Seville,1900–1919年在温州服事),王廉(Mr. Francis Worley,1911–1932年在温州服事),王师母丁志贞(Mrs. Jessie Pettit Worley,1912–1950年在温州服事)。这八位宣教士的事奉,既有相互重合、一起同工的时期,又有彼此衔接、前赴后继的关系。
这几位宣教士并没有传记传世,书中主要资料来源于他们发表于内地会机关报《亿万华民》(北美版和英伦版)的书信和事工报告。非常感谢黄老先生对这几十年的《亿万华民》的阅读和检索,一点点拼凑出他们当年服事的图景。而宣教士在这些书信和报告中,更多记录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,而是当年温州教会的状况、温州早期信徒和传道人的见证。因此,笔者尝试将这本小书中珍贵的史料和自己的读后感加以结合,使读者在浮光掠影般地一瞥那些年内地会系温州教会的成长时,也被其中的见证所激励。
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成长的温州教会
清末的温州,是一幅充满矛盾的图景:钟灵毓秀的山水之间,弥漫着贫瘠与蒙昧的沉疴。百姓贫苦,文教不彰,公共卫生意识匮乏,民间多仰赖鬼神,以致庙宇遍布。与此同时,乞丐与盗匪成为社会痼疾,也对传福音事奉带来威胁。1894年,宣教士谢姑娘(Miss Stayner)在城外村庄探访,不料有匪徒深夜入村,妄图绑架她们索要赎金,幸而接待她们的姐妹帮助她们逃出了魔掌。
因为社会危机严峻,民不聊生,宣教士常成为百姓的迁怒对象。1898年温州发生灾荒,引起暴动,曹雅直的妻子曹明道师母在街上被人打伤。暴动严重时,大部分宣教士要逃到江心屿的领事馆避难。
在温州宣教更为不易的是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,宣教士们常常患病,频繁的瘟疫使得多位宣教士及其子女病逝于温州,戴德生的女儿戴存爱(Maria Hudson Taylor)和她的小女儿便是在温州服事时患痢疾而离世。[2]
温州教会的信徒常常受到逼迫。一是村民花费巨款装修庙宇,每到节期,村民以抽税方式集资,请戏班表演“神功戏”,信徒若不参与,便引发冲突,变成迫害。二是祭祖时全村按宗族辈分出份子钱,信徒必须抉择。因风俗习惯时常被挑战,村民对于信徒就更为仇视,官府又纵容包庇迫害者,使他们有恃无恐。例如1895年,萧家渡的村民以庙中偶像被毁坏为由,逼迫一位慕道友,甚至扬言要烧毁一切信徒房产;而官差收受贿赂,不仅没有维护治安,反而引起了全村的暴乱,福音站新建的牧师住宅和会堂被拆毁。之后知县派兵镇压更引起众怒,焚毁了20栋信徒民房。[3]
总结宣教士余思恩、衡平均分别在1904年、1907年的内地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,除了气候、疫病、逼迫、仇视等艰难外,20世纪初的温州教会还面对五大难题:1)信徒多来自贫穷家庭,没有经济能力支援教会,反而希冀传教士的帮助,信徒原来的工作也常常因信了主而受到亏损,以致失去原有的收入;2)华人传道的教育程度有限,很难对知识分子家庭传福音;3)信徒希望孩子能受基督徒教育,而现有学堂不足以供应需要;4)赌博之风、种罂粟、抽鸦片、文盲等问题严重,教会中只有一成男信徒识字,女信徒则更少,温州人中四百人才有一个受过教育的,故在教导方面只能口传;5)缺乏能以温州方言布道和教导圣经的宣教士。
但在如此艰困之中,内地会系温州教会却在不断扩展。摘录书中所记1902–1921年的相关数据,便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一进程[4]:
1902年,温州城中信徒504人。
1903年,城中信徒627人,华人传道60名,其中37名是义工。
1904年,温州城内聚会人数约1000人,城外村庄至少有2500人。宣教站每月出版一份中文报纸,送到各村镇,让信徒和慕道友有灵粮喂养。
1906年,城内信徒892人。
1907年,温州城内约有900名会友,其中女性约400人,参加聚会的约有1500人。有13–14个分区,每区有会堂,由驻堂牧师主持,并有传道人相辅助。义务传道人周末来教会事奉(类似于带职服事),全职牧师和传道人的生活则由宣教站负担。
1912年,温州宣教区会友约2200人,聚会人数约5990人。130间大小教会和福音堂。有不少平信徒自愿起来协助教会牧养,宣教士除了监督、巡回探访,也在城内举办圣经学校。
1914年,温州宣教站会友共2775人,150处聚会点,40位受薪传道人,161位义务传道人。
1917年,温州宣教区会友约3000人,分别在160多个会堂聚会,有42位驻堂牧师和180多位驻堂传道人。
1919年乡村福音堂增至169个,由带职事奉的本地传道人牧养。差会逐渐推动教会自立,先设立本地长执会,再加上本地和本区的定期联合聚会,期待华人信徒慢慢多负责任,最终能承担所有事奉。
1921年,温州宣教区约有2100位信徒,90个福音站,130位华人传道。大部分福音站由当地传道人负责,宣教士常常去探访他们,支援他们。
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,温州教会的会友人数、聚会点数量一直在稳定地增长。
1902–1921年,正处在从庚子教难后到非基运动前中国教会的一个“黄金时代”,温州教会在此历史阶段中,也快速地成长。但这个阶段并非一帆风顺,实际上天灾、疫病、盗匪仍在持续搅扰着温州的宣教士和信徒。除此之外,从1910年起,温州教会便开始受到“教会自立运动”的影响。当时自立运动的参与者,更多从政治层面、而非教会成长的层面来思考和推动教会的自立、自传、自养,故持续不断地给温州教会带来困扰,破坏教会的合一,影响了一些同工和许多信徒离开。衡牧师对此评论说:“如果他们只传‘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’的话,我们为他们祝福,可惜绝大多数不是这样。故需要代祷,求神施恩兴起中国领袖,来代替宣教士。”[5]感谢主应允祷告,从上述数据中可见华人传道人数日渐增多,除了驻堂的全职传道,也有许多乡村福音堂的本地传道人兴起。他们原是年轻农夫、铁匠、木匠、小贩等,一周勤劳作工后,周末就到各地传道、牧养会友。
温州教会虽然身处各样的艰难之中,却能不断栽培工人出来服事,不断带领人悔改归主,真是显出了福音的能力。这也许是因为多年来教会一直在教导:“我们得救是为了他人也能得救。”
温州教会火热的福音事奉
“我们得救是为了他人也能得救。”这句教导来自内地会最先来温州传道的“独脚番人”曹雅直牧师。他当年到内地会应征时,戴德生牧师问他说:“你只有一条腿,为什么还坚持要去中国?”他回答说:“因为我看不到两条腿的人去,所以我必须去。”这位“必须去中国”的曹牧师,在温州服事了整整二十年,建立了花园巷教会、男校;他的妻子曹明道多做妇女事工,建立女校。在曹牧师病逝后,曹师母继续坚持服事了温州教会十年。
温州还有两位在丈夫去世之后仍坚持服事的女宣教士,共同成为美好的见证。梅师母是苏格兰人,1891年抵华,在温州服事两年后与梅教士结婚。1895年,她不满十个月大的孩子因感染霍乱病逝,一周之后,她的丈夫也安息主怀。梅师母在极度悲痛中仍坚持在禾场上事奉。她在给戴德生牧师的信中说:“父神有祂的旨意,家人全都走了,留下我一人,但我并不孤单,因为主耶稣应许说:‘无论怎样,我会继续与你同在。’神接去了祂的工人,但祂的工作仍须继续下去……我渴慕遵行祂的旨意,祂已经取去我的一切,现在能献上的,就是我的余生。祂先将我倒空,然后以祂的慈爱、怜悯和能力充满我……”[6]此后,梅师母常常到乡村传福音,开办妇女圣经学校,造就了许多人。1914年她与一位服事金华教会的宣教士结婚,之后又在金华工作了13年。当1927年她离开中国之时,已经在浙江服事了近四十年。
还有一位王师母,来自新西兰,1912年被派到温州服事。1932年她的丈夫王廉教士突然病逝,她继承遗志继续服事,负责妇女圣经学校事工。许多姐妹是在她的教导和帮助下信主的。她与温州的信徒一起经历了八年抗战,在战时仍然开办圣经学校,每次学校结业之后都有学生信主。1950年底,64岁的王师母才被迫离开她服事了38年的禾场。
宣教士忠心事主的心志也激励着温州教会的初代信徒。第一代中国基督徒的处境,往往比宣教士更为艰难,四邻鄙夷、亲族不容,但他们甘心为主受苦,并在各样艰难之中将主的道传扬开来。例如神学家刘廷芳的祖母叶氏,她原是一位大家闺秀,丈夫去世后独自养育幼子,因为在婆婆的丧事中拒绝跪拜死人,而被夫家亲族逼迫,只给她1/16的遗产,使她生活难以为继。但她后来却成为曹师母的好助手,负责女校工作,又成为温州教会的第一位女传道。又如永嘉县第一位受洗信徒张砥(音译),他本以摆渡为生,在主日义务载无力付船钱的信徒过河聚会。义和团暴乱中,他常受村民威胁,却宁死不屈。后来他成为一位基督的工人,在宣教站中工作。他的妻子曾是女校学生,也引领许多人归主。
因城外会友居住分散,宣教士们常常结伴而行、下乡探访,到哪一处福音堂,就在哪一处布道,也在信徒的家中向邻居们布道。在宣教士们的榜样和教导的激励下,温州教会的信徒格外火热地传福音。他们亲自向亲友邻舍传福音、作见证,趁新春放假也会展开特别的传福音工作。例如夏时若牧师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:“1914年1月26日大年初一,温州城内中、南和西三堂,约有70位信徒,两三人一组作伴,在城外村庄、城内街道,逐家分发福音单张、售卖福音书,共分发了2500份。初五下午,全体回到会堂报告,反应非常好,不常开口传福音的,也找到听众;但仇敌反对力量也大,不肯接受单张的、反对和反驳信仰的比比皆是。”[7]
为了趁此机会鼓励信徒广传福音,教会紧接着举行了强调传福音的培灵会和圣经学校,教导并推行个人布道,采取“一领一”的方式,邀请未信者来布道会。1914年2月14日下午,“一领一福音队” 成立,约有50个成员,立志做三百日传福音工作,要在有限时间内把福音传遍全区。还有些人奉献金钱,用来支持外出传福音者一切的费用。1914年年底最后一次施洗时,受洗的人数达到151人,为历年之冠。
温州的妇女事工格外有成效,衡平均师母1890年刚来温州时,看到妇女们很少出门,更少人识字;而1917年,已经有许多妇女带着圣经和诗歌本前来聚会。教会的妇女查经班每周主日进行,还有不少男子来旁听。教会又在农闲时间举办妇女圣经学校,邀请各村妇女来宣教站住一个月,白天查经,晚上有专题讲道。许多妇女因此归主,又因为努力学习,就能用神的话向其他女子传福音,从信徒成长为工人。宣教士们感受到,妇女圣经学校是向妇女传福音和栽培信徒的最好途径。这样栽培,建立了不少十分爱主的姐妹,她们除了向邻舍传福音外,还两人一组下乡布道,不少村庄福音堂,都是由她们传福音开始的。
学堂事工也给温州教会带来祝福。女校中多数女孩在离开学校前已信主,她们多成为传道人的妻子,也有嫁给农夫和商人的,她们都把信仰传给下一代。而男校的许多毕业生都成为教会的义务传道人。
温州的信徒爱慕主道、热心传道,不仅表现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,就是在天灾人祸带来社会动荡的时候,他们也为他人灵魂的得救费时费力。1929–1930年,温州发生大饥荒,教会不仅救济灾民,也在灾民中传福音。女宣教士带领着一队队姐妹们,到流落在街头和寺院里的妇女、孩童中传道。那时虽盗匪横行,教会仍有一支四人福音布道队,去不常有人传福音的地方传福音,白天两个两个地出去,逐家个人布道和发单张,晚上则四人合力开布道会,事工很有果效。
抗战中,温州被占领后,牧师被毒打,会堂驻扎军队,但教会仍轮流在各信徒家里聚会崇拜,城外农村福音堂每主日仍经常举行主日崇拜。温州难民南下,其中的信徒们仍在随走随传,成为难民中的无名传道者,而且那时温州仍有福音布道队。有一位不知名的姐妹,在抗战时期,带着孩子们逃到一个荒僻村庄,主日清晨爬上山祷告读经敬拜。她的举动引起村民的好奇,就邀请她传福音给他们听。于是她一周周聚集村民,向他们传福音,带领村中孩子唱诗歌。后来她联络上温州布道队,布道队立即前往,那村庄就有多人归主。
1942年2月至4月,趁着战事稍缓,教会坚持在四间不同的福音堂举办了四期妇女圣经学校。王师母在信中写道:“虽然物价高涨,但我们仍有193名妇女参加,真是令人兴奋。为着省钱,有两处福音堂的学生用番薯皮混合的小饭团果腹,另外两处则差不多晚上全部回家。学生们对功课的投入和对课程的兴趣,令我们感到喜不自胜,主与我们同在,每处都有人决志信主。”[8]
1949–1950年,温州教会仍坚持开办圣经学校,教会的生存环境虽然越来越恶劣,传道人也被逼迫和囚禁,但是到1950年底,仍有300人受洗加入教会。
类似的记述还有许多,虽然都比较简短,但却使我们看到神赐给祂儿女的,真是“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”(提后1:7)。黄老先生没有对任何一位人物的事迹多加渲染,但书中这些平实简洁的文字,如含在口中的橄榄,思想回味时方体会到当年宣教士和信徒对福音的热忱,对神事工的忠心和舍己。他们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中,聚会不停,传讲福音不停,训练门徒不停,真实地见证了“炎热来到,并不惧怕;干旱之年,结果不止”(参耶17:8)。
结语
合上这本小书,便有一句经文涌上心头:“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,站立得稳,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”(腓1:27)书中所记温州教会的成长,正是一家家人、一代代人“前赴后继”的结果。无论是西方宣教士,还是中国传道人和信徒,都有着迫切救人灵魂的心,而他们的服事也结实累累。宣教士离开中国后,温州教会处境越来越艰难。1953–1959年,有形教会被摧毁。1959年温州竟成为“无宗教区”试点,然而第二年,温州教会在信徒家中的聚会便开始了。[9]在文化大革命中,福音快速传播,信徒甚至藉着婚礼和葬礼的机会布道。九十年代,温州的福音事工更为复兴,温州的商人潮、学生潮也将福音带到全国各地。思想这些历史,又对照这本小书,不由感受到温州教会对福音的火热、对聚会的坚守、对主的忠心,都能追溯到几十年前的源流。由此,就更令我们感受到,服事基督的教会该当如何谨慎地用金银宝石建造。当下的事奉既是及时地撒种浇灌,也将形成属灵的传承。
[1] 后来循道会也差遣了多位宣教士来到温州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慧廉(William Edward Soothill)。
[2] 黄锡培,《昔我往矣——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》(香港:海外基督使团,2014),51–52。
[3] 黄锡培,《昔我往矣——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》,25–26。
[4] 这些数据和史料若无特殊说明皆引自书中,因避免繁琐没有注明出处。
[5] 黄锡培,《昔我往矣——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》,17。
[6] 黄锡培,《昔我往矣——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》,29–30。
[7] 黄锡培,《昔我往矣——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》,71。
[8] 黄锡培,《昔我往矣——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》,94。
[9] 舍禾,《中国的耶路撒冷:温州基督教历史(下册)》(台北:宇宙光全人关怀,2015),495。
 《教会》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
《教会》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